跑步是一門藝術
2016-08-04
跑步是一門藝術,而跑者則是藝術家嗎?最好的答案,就是畢卡索的答案。有人曾問他:「什麼是藝術?」他回答:「什麼不是呢?」
因此,跑步跟我們做的其他每件事一樣,都是一門藝術。當我跑步時,我知道這句話是對的。不論我的表現多麼平凡,跑步是我的藝術,而我就是藝術家。跑步之於我,猶如舞蹈之於他人。跑步是最古老高尚的藝術,我的祖先在會跳舞之前,就會跑步了。跑步給予我形式與實質的完美結合,而非舞蹈。
跑步也符合赫伯特.里德(Herbert Read)的定義。他說,藝術是從混亂中逃脫、是編上號碼的動作、是受尺度限制的物質、是尋找生命韻律的素材。你幾乎可以相信,里德寫下這個定義時,眼睛正在盯著跑者。
還有哪裡更適合逃避混亂及尋找秩序?還有哪裡會把動作根據步伐、呼吸、分鐘、英里做更多編號?還有哪裡會對空間、物質、跑者的精瘦,及道路的漫無止盡下更明確的定義?至少對我而言,還有哪些其他地方,可以尋找生命的韻律,可以聆聽身體,聽它談論我的靈魂?
因為身體變成了靈魂,靈魂變成了身體,所以跑步會是一種整體經驗。跑步是藝術,而且不僅止於藝術。其本身提供了高於其他藝術的思維和抽象。某位畫家曾說:「我需要好幾個小時閱讀,接著思考我所閱讀的東西,整合,然後獨處。與此相較,花在畫布上的時間其實微不足道。」

另一方面,跑者一直都在這塊畫布上。他一直在觀察、感受、分析、冥想;一直在捕捉儲存偏見的前意識(preconscious)。這個前意識頑固地拒絕用我們過去的經驗照亮現在,而跑者在它前方探索本能和情緒,甚至下沈到,只能稱之為神祕的狀態。
跑者的失敗之處,是身為一個藝術家。他可能有能力表達這些感受和洞悉,而且或許他表達了,但無人看見。他沒有做到藝術家的主要功能,傳達他對曾經有過的情緒的瞭解。即使能在不同高度來觀察生命的詩人,也幾乎是在同一個平面上看待跑者。
「他獨自出現/出現,然後經過/獨自一人、已是足夠。」孤獨、移動、充足就是跑者。世界對他並沒有更多的認識。
這一切會隨著時間改變。跑步是一門古老的藝術,只是最近再次流行起來。我們還在學習,如何擬定完整的回應。在交通繁忙的地方,我可能像巴斯特.基頓(Buster Keaton)一樣面無表情。但在孤寂的道路上和空虛的叢林裡,我的內在正變得清晰起來。在那裡,我回應了青草、泥土和落葉。我的跑步是陽光和陰影的一部分,也是吹拂過我臉上與背部的風兒。如果你看見我,就會看到得意、熟練、掙扎、挫折和絕望。我流露出憂傷和憤怒、怨恨,還有對狗、人和高地的恐懼,對黑暗、迷失和孤單的恐懼。
但別人瞭解我們與否很重要嗎?尤其是跑者以外的人?我們不一定要勸說他們親身嘗試跑步,而是要鼓勵他們,尋找他們自己的藝術,成為自己的藝術家,聆聽內心的聲音,那聲音正在呼喚他們,以自己的方式存在於這個世界。
跑者知道這個必要性。我知道,雖然我可以自由選擇做任何一種人,但我堅持要做一名跑者。奧特嘉是這麼說的: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一種人。但唯有選擇特定的種類,才能做你必須做的那種人。」
在跑步時,我逐漸瞭解奧特嘉的話。我已經找到我特定的種類,聽到呼喚我的聲音,找到我的藝術。我體驗與詮釋生命的媒介。我不擔心,跑步不足以達成這個任務。威廉.詹姆斯曾提到,一位年輕人正在學習自己和他的本能及情緒:「在缺乏實際物資的時候,運動拯救了他,並協助他完成了教育。」我明白,他所要傳達的真理。
書籍資訊
◎文字摘自遠流出版,喬治‧席翰著作《我跑步,所以我存在:美國跑步教父關於運動的18種思索》,這是一本1978年問世以來,38年間深受讀者歡迎,歷久不衰的跑者聖經!
「我們每個人都很獨特,天生就具備與其他人不同的潛能。
成功來自於發現真正的自己,做自己,開發自己未開發的潛能。」
◎跑步,一種全面的體驗……
為什麼跑步?為什麼運動?不只是為了健康,更是為了「超越」。同時,這也是內心的催促。運動不是化驗,而是治療;不是磨練,而是獎賞;不是問題,而是答案。
美國跑步教父席翰醫生,作為慢跑風潮推手的他在本書中,剖析跑者的身心靈,並援引文學、哲學、心理學、醫學等與運動相關的觀點,從作息的調整、體態的訓練、心靈的整合,到跑步時的掙扎拉拔、賽後心境的舒坦與超脫,皆有動人且深刻的描述。
我們可以從這本書裡,看到一個平凡人為了所愛之事,奉獻出他最偉大的堅強、無法摧撓的意志與勇氣,他步伐不停地練習生活、尋找真實、體驗純粹,堅持活在自己的水準之上。
翻開這本書,我們不能保證,你會從此熱愛上跑步或任何一項運動,但你絕對會因此得到激勵,想要開始嘗試跑步或者運動,並且從中得到自然的快感、真實的超脫,甚至追求你真正渴望的人生!
書籍資訊 請點此
◎文字摘自遠流出版,喬治‧席翰著作《我跑步,所以我存在:美國跑步教父關於運動的18種思索》,這是一本1978年問世以來,38年間深受讀者歡迎,歷久不衰的跑者聖經!
「我們每個人都很獨特,天生就具備與其他人不同的潛能。
成功來自於發現真正的自己,做自己,開發自己未開發的潛能。」
◎跑步,一種全面的體驗……
為什麼跑步?為什麼運動?不只是為了健康,更是為了「超越」。同時,這也是內心的催促。運動不是化驗,而是治療;不是磨練,而是獎賞;不是問題,而是答案。
美國跑步教父席翰醫生,作為慢跑風潮推手的他在本書中,剖析跑者的身心靈,並援引文學、哲學、心理學、醫學等與運動相關的觀點,從作息的調整、體態的訓練、心靈的整合,到跑步時的掙扎拉拔、賽後心境的舒坦與超脫,皆有動人且深刻的描述。
我們可以從這本書裡,看到一個平凡人為了所愛之事,奉獻出他最偉大的堅強、無法摧撓的意志與勇氣,他步伐不停地練習生活、尋找真實、體驗純粹,堅持活在自己的水準之上。
翻開這本書,我們不能保證,你會從此熱愛上跑步或任何一項運動,但你絕對會因此得到激勵,想要開始嘗試跑步或者運動,並且從中得到自然的快感、真實的超脫,甚至追求你真正渴望的人生!
書籍資訊 請點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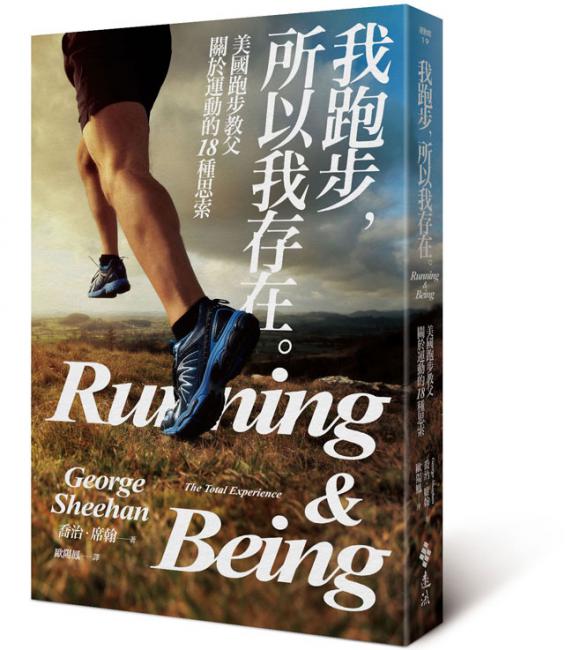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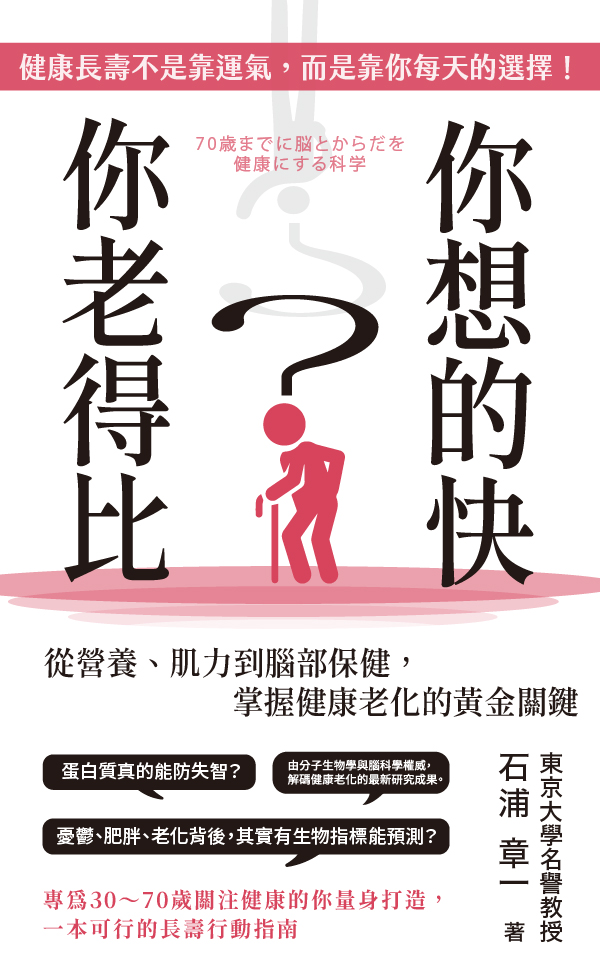

運動星球
戶外跑步補水太多 小心馬拉松選手三大死因「低血鈉症」
2019-07-16
大熱天到河濱練LSD時,大家都應該知道要多補充水分,但小心!如果不慎補充過多水分,恐怕引發馬拉松選手在比賽中三大死亡原因﹕低血鈉症。

戶外跑步補水太多 小心馬拉松選手三大死因「低血鈉症」 ©womensrunning.com
低血鈉症是什麼﹖
低血鈉症(hyponatremia)是體液及電解質失衡的一種症狀,以致血漿內鈉濃度不正常地低於135 mmol / L(正常的血鈉水平為136- 142 mmol / L)。持續的低血鈉水平會導致水分急促地湧進腦部,造成腫脹與一系列的神經紊亂(神智不清、昏迷),嚴重者腦幹會受到破壞,造成死亡。
當血鈉的水平下降至125-135 mmol / L時,一般不會有明顯症狀,有些人會出現不嚴重的腸胃障礙(如反胃)。當血鈉水平達125mmol / L以下,症狀會變得明顯且嚴重,如頭痛、嘔吐、氣喘且帶響聲、手腳腫脹、坐立不安、不尋常的疲累、神智不清等。如果血鈉水平降到低於120mmol / L,會出現呼吸停頓、昏迷、永久性腦部受損,甚至死亡。

血漿內鈉濃度不正常地低於135 mmol / L為低血鈉症
這些跑者小心! 低血鈉症風險高
在馬拉松賽事中有三個主要死亡原因﹕心臟病發作、低血鈉症與中暑。你無法預防心臟病發作,也較難防止中暑,但低血鈉症是可以透過計算和控制補給避免的。
在一場全程馬拉松比賽中,因水分流失使體重減輕2-3%,通常算在安全的脫水範圍內。然而,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(NEJM)的一項研究指出,許多馬拉松選手在賽後出現低血鈉症現象,主因在比賽中補充過多水分。該研究針對2002年波士頓馬拉松的488位完賽選手調查,其中有13%跑者出現低血鈉現象(135 mmol / L);0.6%的人出現嚴重低血鈉現象(120 mmol / L),而且女選手和BMI較低的選手較易出現低血鈉症。研究作者推測,可能因為女選手跑得比較久,和性別並沒有關係;而體重較輕流失的水分相對較少,因此最後補充的水分佔體重的百分比就越大。
總體來說,當跑者長時間運動中喝太多水(1小時內喝進3公升或以上),出現低血鈉症的風險就會提高。此外,個子矮小(只需較少的水分就可以稀釋體液)、出汗較多、跑速較慢(運動時間相對較長)的跑者,出現低血鈉症的風險較高。

個子矮小、出汗較多、跑速較慢的跑者,出現低血鈉症的風險較高 ©Pierre-Selim Huard
如何預防﹖
1. 了解自己需要補多少水
每個人的汗液流失速率不同,所以該補多少水也有差異。一般來說,在運動進行中就算不覺得口渴,40公斤以下兒童每15-20分鐘應喝150毫升的水或含鹽飲料,成人則應喝進250毫升;此外,運動前2小時應先喝400-600毫升水分。你可以在平時練跑先使用上述平均補水值,量測跑步前後體重的差異,再依照這個差異做調整。
2. 跑步中補給鹽錠
鹽錠在馬拉松賽的補給站、跑者私補中,已算是相當常見且普及的補給品。跑步期間適量補充鹽錠,可有效對抗低血鈉症;至於常見的補給「果膠」中也含有鈉成分,份量可先查詢其包裝上的營養成分欄。
資料來源/NEJM、香港體育教學網、維基百科、Runner’s World、GU
責任編輯/Dama

運動星球
超輕感太空科技的Reebok Floatride輕量緩震長跑鞋
2017-09-06
體驗獨家科技跑鞋Reebok Floatride 感受太空中的羽量輕盈
Reebok先前聯合專業機構發表超輕量Reebok Floatride Space Boot SB-01太空鞋履,搭載因應新世代航太科技而生的緩震中底Floatride Foam。全新上市的Reebok Floatride跑鞋,採用與太空靴相同的中底科技,獨家Floatride Foam輕量緩震材質,提供跑者絕佳的避震回饋體驗,黑白酷炫新色強勢登陸,腳踏太空再也不是夢。

超輕感太空科技的Reebok Floatride輕量緩震長跑鞋
Reebok Floatride獨家緩震中底搭配黑白新色強力襲台 潮流型格引領全新跑鞋時代
Floatride使用獨家跑鞋科技Floatride Foam緩震中底,以更輕量化的高強度緩震結構材質,提供卓越避震效果,同時兼具舒適柔軟腳感;全足環形EVA鞋底,讓跑動的每一步都保持絕佳平衡,感受能量完美流動;搭載高透氣Ultraknit針織鞋面,讓Floatride的靈活步態特性發揮的更淋漓盡致,避震回饋能量交替更順暢。9月9日,年度矚目科技跑鞋Reebok Floatride將搭載太空科技強勢亮相,搭配黑白酷炫新色強力席捲全台,宣告全球新跑鞋時代震撼來臨。

粉紫配色搭配全足環形EVA鞋底,讓跑動的每一步都保持絕佳平衡,感受能量完美流動

Reebok Floatride搭載太空科技中底正式亮相 正式宣告全球新跑鞋時代正式來臨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