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運動星球
因為,山,就在那裡
2017-01-04
給我一個走下去的理由
大霧中,近在咫尺的樹林一片迷茫,
什麼都看不見之後,就只剩下自己。
我被寒冷驅策著向前,
再疲累都不能停下腳步⋯⋯
痛苦。
腦海中確切出現這個詞的時候,心裡有些震驚,為著我甚少在山上這麼想。從前再苦也不覺痛苦,是自己想上山,苦樂皆理所當然。但如今只想忘記當下……惡劣的天候讓人無法集中更多的注意力,這些意識稍閃即逝,剩下機械式的身體動作,腳步沉沉地拖向前,濕透的登山鞋真重,山徑都被雨水弄糊了,像小溪一樣嘩嘩流去。
我抬起頭,視線被雨衣的帽沿遮住,灰白色的大霧裡什麼也看不到,走在前頭的隊友不知在哪裡,連近在咫尺的樹林也是一片迷茫。
什麼都看不見以後,就只剩下自己。
聽見自己的喘息聲,感受到心跳分明。喘息聲急促而清楚,大口呼進的冷空氣似乎無法為身體帶來能量,我偶爾會拍拍自己的大腿、搓搓自己的臉以示鼓舞,自我打氣的最後,有些恍惚,所有努力好像都是一場夢。
用緩慢的龜速挪移,儘管心底不斷地吶喊:「休息吧!」但只要一停下來,全身就不由自主地發抖,受不了只好咬牙繼續走。我被寒冷驅策著向前,再疲累都沒法停止腳步。選擇在二月上高山,是要有點意志力才行。
這會兒,人人都在家裡頭團聚,圍爐過好年,我想像溫暖的燈光籠罩著老家,電視機咚隆咚隆地慶賀新年,弟弟轉台尋找最精彩的新春特別節目,一邊小阿姨打電話外訂珍珠奶茶,大家亂七八糟地喊著半糖去冰全糖少冰,混亂中有人丟一手牌到桌上:「差一點就同花順了!」
冷雨從昨天到現在都沒有停過,一分鐘都沒有。雨水偷偷滲進雨衣,手臂能感覺水珠的滑行。我在心中恨,恨昨日帳內沒把雨褲縫合,雨褲內層破了大半,下了太久的雨滲進褲子,因毛細現象慢慢擴散到整個下半身,溼冷的褲子包覆大腿,走出密箭竹林的同時,感覺到連內褲也溼透。冷風一吹,簌簌發抖。
我為什麼在這裡?
路不好走,連日的雨讓山徑變得鬆垮,眼睛只能專注地盯著地上,稍不留神就可能踩空。走在山腰,之字繞行,我再次質詢自己:為什麼?幾個人約好在年假上山,那些年前的殷殷期盼,而今想來真是荒唐!
看了一下錶,早上十點十二分,該換衛生棉了……一邊往上爬一邊在心中反覆掙扎,意志力一點一點消散,這種時候我完全不想在溼淋淋的樹叢裡蹲下脫褲子,一點也不想。逕自埋頭走著,逃避性地忘了生理期的事實,以為經血會凝結在冰冷的雨水裡。

高義翔攝影/果力文化提供
虛弱的意志力
想起今早,在太平東西溪合流口邊坡的營地,一夜大雨過後,我和瓜瓜躺在帳篷裡,感覺到下背的潮溼,兩人都不想面對事實。
「給我一個走下去的理由……」淋了兩天的雨,我拍著自己溼了大半的睡袋,向瓜瓜求救。
瓜瓜坐起,拿著角落的鋼杯,喝一口剛剛煮好的熱可可,因為睡袋潮濕並不膨鬆的關係,今天她收睡袋收得很快。
「告訴我啊……」我盯著她,翻起身來意興闌珊地吃著早餐,一盒因打包不良而被壓碎的蔬菜餅,食之無味。
瓜瓜坐在帳篷門口,躊躇許久,她煩躁地抓了抓頭:「走完……走完可以……走完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意志力……」她的聲音愈來愈小,「意志力」三個字在最後幾乎聽不見。
我瞇起眼,抿嘴一笑:沒錯,這是我聽過最虛弱的答案。
「高義—給我們一個走下去的理由!」瓜瓜瞪著我嘲諷的嘴臉,對著隔壁帳的嚮導大喊。
「你們的睡袋有沒有溼掉?」高義的聲音從那帳傳來,儘管雨持續下著,還是可以聽見他和歷凡打包的細碎聲響。
當我們立時異口同聲,以近乎咆嘯式的聲音用力回答:「有— !」,憤怒以一種高漲的形式傳響整個山谷。
只聽見高義說:「太好了,原來不只有我一個人。」
瓜瓜立時翻了白眼,我望著漫天細雨,了解到睡袋無一倖免的事實,興起撤退的念頭,今天才第三天……摸著身上這件唯一乾燥的保暖刷毛衣,突然害怕有天它也會淪陷。氣象報告說這波寒流將使台灣降雨一周,想到往後每一天都可能在雨天走路,晚上再鑽進冰冷潮濕的睡袋裡,任誰都提不起興致。
「給我一個走下去的理由……」我看著瓜瓜,她拉開帳篷前側的拉鍊,坐在帳篷入口已經很久了。
「我不想出去打包……」她低著頭,嘆了一口氣,上半身探出去,用食指和中指不甘願地把泥濘中的登山鞋拖過來。
「睡袋變重了……」我掂了掂收好的睡袋,癟起嘴。「真的嗎?」瓜瓜接過我的睡袋,她的眼瞪得老大,然後毫不客氣地大笑。
「笑屁啊!妳的也差不多吧……」我撇撇嘴角,悶哼了一聲。
雨、雪、冰雹齊下
想著早上的那一幕,感覺大背包又更沉一些。落在身上的雨不知什麼時候變成了冰晶,我抬頭,漫天細小的白色冰雹,掉到地上會彈起,打在雨衣上即刻滾落。
又走了一會兒,才發現同時也下雪了,白色小點輕飄飄的,落到身上沒多久就化了。
這個時刻才察覺,路有些不對勁,剛剛明明很開闊,這段怎麼這麼陡?前面有一棵盤根錯節的大樹,我沿著它的枝幹,艱難地爬升幾米,聽見自己濃濁的呼吸聲。路不見了,野草蔓生,一轉頭,才發現要回去也不好下攀了。
我站在那裡,大背包壓著肩頭,水滴不停從帽沿掉下來,手指頭凍僵了,前天在林道上被螞蝗咬的傷口還在脖子上隱隱作痛。
「歷凡—」站在大樹腰際的邊側,小心地踩在鬆軟的泥上,我對後方大叫。
沒有聲音,除了自己的呼吸聲,雨、雪、或冰雹都不重要了,我不想動,多麼希望這裡就是營地。
「歷凡— !」我再叫了一次。
歷凡的聲音在我的右側,我一邊苦笑一邊尋思怎麼下切,走錯不是第一次了,走著走著就偏離了正路,不夠靈敏的路感一直帶給自己不少麻煩,在這雨雪和冰雹都分不清楚的時刻更加令人沮喪。
想回家。(爬山這麼多年,從未走到一半想回家過。)
「在這裡,妳直接橫切過來—」歷凡察覺我走偏,對這頭大喊。
我緊緊抓著生長在鬆軟泥土裡的箭竹和草根,生怕一個不小心就墜落,像螃蟹一樣橫著走過,大背包卻拉著自己不斷後仰。
走到他面前的時候,風雪中等待的他看來也頗為狼狽。
我卸下背包,正午時間早過了,寒冷超越了飢餓,兩個人一邊發抖一邊吃巧克力,相對無言。
我想跟他說我要回家,又覺得這樣做不夠成熟,這種天氣,大家走起來都很煎熬,實在不該說任何的洩氣話。
「妳戴著吧!」歷凡從頭袋裡掏出防風的保暖手套。
「不要,你留著自己用。」我艱難地剝著巧克力的包裝紙,手抖到巧克力都拿不穩。
「我的手不冷。」他拿著防風手套,遞給我的手停留在空中。
我看著他,接過手套。雙手沾滿了剛剛橫渡過來的泥土,也不管就把巧克力送進嘴裡,行動遲緩的套上手套,凍僵的手指卻不聽使喚。
「這樣才套得進去……」歷凡來到跟前,協助我戴好手套,轉身續往上走。
感覺乾燥的絨毛包覆手心,風再吹不進來,我握緊拳頭,覺得可以繼續走下去了。
等待一碗泡麵
不記得我到底走了多久,跌跌撞撞地走,箭竹林或大草坡都一樣,偶爾能看到歷凡在前面駐足等我。
走到一個溪溝,看到高義蹲在那裡煮泡麵,瓜瓜縮在一個角落等待。
在那當下的視線裡,他們兩人的存在本身比那杯泡麵更真實,我以為以我的腳程,今天要到營地才能看到他們了……心裡很高興,儘管表面上沒有任何舉動。
「都沒停下來吃中餐吧?等一下,泡麵快好了……」高義的聲音在發抖,他一定在這邊等了很久。
我只是站著,就只是站著,連背包也不想卸下。
「幹,這什麼天氣……」瓜瓜低著頭,罵髒話的聲音很微弱。
「都這個時候了,我就想大家一定要吃點什麼熱的才行,不然會走不下去……」高義是唯一做事的人,他的背包打開倒在一旁。
雨持續下著,我們的身體不斷地滴水。四個人不停地發抖,煎熬難耐地等待著一個鋼杯滾沸。
高義把泡麵遞到我面前:「妳先吃。」泡麵因為他發抖的手而微微搖晃著,我盯著他的手,因高山水腫而微胖,不知怎麼整隻手凍得發紅。
那是一馬當先做事的手,只感覺鋼杯熱呼呼的白氣衝上自己的臉。
「高義你很冷?」我說。
「妳先喝,溫暖身子以後就慢慢走,不要停在這裡。」高義說。
我點點頭,熱湯緩緩流過喉頭,一股溫暖默默蔓延五臟六腑,捧著鋼杯的手突然有了溫度。
我坐在一塊大石上吃泡麵,三個隊友在身邊,高義不停地踱步和搓手;歷凡坐在大背包上發呆;瓜瓜不動,臉上沒有任何表情。
太冷,他們無神地等待著一碗泡麵,沒有多餘的交談,沒有人催我。
「瓜瓜妳今天走得也太快了……」我一邊喝著泡麵的湯,一邊說。這傢伙兩天總跑在前頭,連高義也追不到。
「沒有辦法,我沒有辦法停下來……等你們等好久喔!」瓜瓜抬起頭,終於開口。
「我今天狀況很差……」瞄了一眼歷凡,謝謝有他跟我一起走在後面。
「沒關係,我也是,全身上下沒一處是乾的……」高義說。
「我也是!」用力宣告,像遇到知音一般。我站起來,把鋼杯拿給高義,他沒喝,直接遞給瓜瓜。
似乎,找到為什麼我們在這裡的意義了。
彷彿過了一個世紀那麼久
我允許自己停下來喘氣休息,但不會太久。該走時我會對自己喊話:「走!」每次「走!」這個字都會說得很有精神。自此以後一路我經常和自己說話:「可以的!」、「不要停。」、「不能睡!」……好像只有這樣,才不那麼在意風雨。
又下冰雹了,它們集體降落的速度很快,放眼看去像是下大雨,如果不置身其中,白茫茫一片其實也很美。
「你還真能下啊……」我看著漫天飛舞的冰雹,在心底驚嘆天空的不止息。
歷凡給的手套在穿越幾段密箭竹林以後,漸漸死去。防風的材質使得水封在裡邊出不來,手稍稍使勁就能感受冰水包覆,最後的溫暖遠走,開始無法控制身體,就算一直保持走路的狀態,還是從頭到腳都在顫抖。一旦停下來,如果不是雙腳不聽使喚,抖到自己都站不穩,閉上眼我立時就可以睡著。
「失溫」兩個字閃進腦海,開始感到恐懼。到後來,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走什麼樣的路,努力令自己清醒,想盡所有藉口都無法勸服自己繼續走,我好想念男友小飽,僅依恃對小飽強烈的思念走著,眼裡只裝得下辨識路徑的路標,此外一切與我無關。滿腦子都在祈禱今天的營地會突然出現在眼前,滿腦子只是狂想山下所愛的人事。意識和身體叛逃了所在之處,不承認自己在當下,連最後一點找路的意念都消失殆盡了。
歷凡跟上來,我沒有回頭看他,停步在邊側:「你先走。」
我們一前一後,陡下到一處乾溪溝,溪溝很滑,上面有青綠色的苔蘚。我知道快到了,只是路標的位置有點奇怪,歷凡回頭望了一下我,說:「妳留在這裡,別亂走喔!」就卸下背包去探路。
等待的感覺很無力,恍惚間有些擔心瓜瓜,依她的腳程,應該早到營地了,太平溪源是空曠的大草坡,她找得到避風的地方嗎?帳篷內帳和營柱都在我這裡,她一個人先到了要怎麼辦?
現實來得很快,我迅速被等待的溼冷征服。一個人在溪溝裡惶惶然,不知該走向何方。歷凡回來,說:「路在上面。」我們回頭,上攀一個地形,失去任何意念僅僅就是走,轉彎卻看見太平溪源。
長跑比賽要到終點之前,總覺得最後一小段路特別漫長。風很大,我沒有任何心情欣賞,天色漸暗,逕自走在迷濛大霧裡,草坡軟軟的,平整的地勢稍稍安撫了我們。撐著登山杖,踩石頭過溪,我的腳步終於加快,他們在哪裡?
高義和瓜瓜不知怎麼搭好的帳篷,在開闊的草地上風雨飄搖。
「幹!終於到了……」歷凡卸下背包,飆出一個髒字。
「你們什麼都不要管,掏了乾衣服就趕快進來!」帳篷裡的高義對我和歷凡大叫。
我把背包卸下,手卻無法隨意志行動,動作遲緩得不可思議。
背包的防水袋一打開就被雨淋濕,聽見自己的牙齒打顫。
「只要拿乾衣服就好,其他都不要管,快進來,我煮好熱的了!」高義大概察覺了我們行動上的困難,又在帳篷裡喊著。
儘管腦袋督促著自己快點快點,但身體沉浸在寒冷中無法自拔。我顫抖著翻開上層的東西,抽出乾燥的保暖外衣和風衣,心想再不快點這些衣服也要溼了,彎著腰,一手拎著乾衣服、一手笨拙地把防水袋封起來、套好背包套,走到帳篷前細碎的毎一步,彷彿都像過了一個世紀那麼久。
「高義,我要進去了—」聲音和蚊子一樣。
帳篷拉鍊被拉開,我看見了高義和瓜瓜,小心地側身在帳篷門口蹲下,想要脫登山鞋。
「妳幹嘛?直接進來!」高義說。
「可是鞋子……」我說。
「不是說通通都不要管嗎?」高義說。
仔細一看,帳篷裡他們兩人為了挪出給我和歷凡的位置,縮在兩個角落,腳上的登山鞋都沒有脫下,帳棚底側有一些混濁的咖啡色泥水。
「你們……」我失笑,不客氣地一屁股坐在帳篷裡,在他們兩人之間。高義遞來一個鋼杯,是加了紅糖的薑茶。
「誰還有心情在那邊慢慢脫鞋啊,先換乾衣服!」瓜瓜說。
脫下溼透的襯衫,高義接過,襯衫被毫無尊嚴地扔在角落。我猶豫著要不要連排汗衣也脫掉,歷凡發顫的聲音在帳外響起:「我……可以進去了嗎?」

趙冠盈攝影/果力文化提供
用體溫互相取暖
小小的二人帳裡擠了四個人,一杯薑茶輪流喝著,我們終於到了不會下雨的地方,背包丟在外面,什麼也沒帶進來,沒有人想移動。
瓜瓜雖然只背了外帳,所幸高義正好背了另一個帳篷的內帳和營柱,儘管兩個帳篷規格不同,外帳還能簡單地罩在高義這帳篷的骨架之上,在這個時刻,不啻為一個遮風避雨的好地方。
薑茶入喉幾多回,我還是不停地抖著。這四個人,爬山這麼多年,各自經歷山上大大小小的慘烈,是我的記憶力太差?好久沒看到這麼潦倒的帳篷了,莫名有些想笑。
喝完的鋼杯歪倒在一旁,登山鞋帶進來的泥水在帳篷底部輕輕搖晃,四個人艱難地縮在那裡,什麼也不想做:不想出去不想掏公糧不想搭帳篷不想煮晚餐……我們失去了把握當下的理由,急著想撇清現在。我想起背包裡沉沉的睡袋,一點也不期待營地的夜晚。
「如果有人問我寒假隊伍的心得,我只有三句話奉送給他。」還在讀研究所的瓜瓜沒頭沒腦地突然說了這麼一句。
「哪三句?」我有些好奇,順勢問。
「第一句『刻骨銘心』。」
「嗯。」我點點頭,可以這麼說。
「再來是『不堪回首』……」語畢帳篷裡一陣哄笑,混雜著我「沒錯沒錯!」的嚷嚷,一時也頗為熱鬧。
「最後一句:不必再提!」瓜瓜撇撇嘴,悶哼了一聲,我們齊聲大笑。
「靠!我到的時候超害怕的,一直等都沒有人來,還懷疑是不是自己走錯路……」瓜瓜說。
立時想到我在溪谷裡的憂心。
「等到都快失溫了,想說不煮點熱的不行,雖然我一點都不想動。我很認命地掏爐頭鋼杯喔!我真的掏了!好在我有帶傘。我就撐著傘,蹲在那裡點打火機……幹!打火機溼了,怎麼點都點不著,我又換一個,點超久的,想說怎麼辦怎麼辦?一直試還是不行,然後高義就到了……」瓜瓜說起自己剛到營地的情景,她講得很快,激動得比手畫腳。
「一個人點打火機的背影真的很可憐。」高義苦笑著。
「好險我出門前,老婆臨時塞給我一件羽毛衣。」他雙手抱著自己,身上那件紅紫色的羽毛衣看起來非常溫暖。
「你真難得會穿羽毛衣。」歷凡說。
「我一到就跟瓜瓜說搭帳,一口氣把溼衣服通通脫掉,只穿這件羽毛衣就進來了。」高義說這話時,語氣裡有一絲得意。年紀最大的他已經有兩個小孩了,爬山對他而言是一種奢侈,要排除萬難才能上山的。
「你的溼衣服呢?」我問,除了鋼杯爐頭、薑和紅糖,家徒四壁的現在似乎什麼也沒有。
「丟在外面。」高義說。
我們交換著各自的落魄,躲在帳篷裡訴說今日的遭遇,聽瓜瓜持續抱怨著打火機怎麼可以這麼對她、聽高義說他過溪跌倒閃到腰、聽歷凡喊著帳篷積水他的屁股又溼了……
雨不曾停歇,一直這麼下。
「哪時候出去?帳篷還要重搭。」歷凡看著外面,天就要黑了。
一時無人答腔。
「等雨小一點再出去吧。」高義說。
雨沒有變小,我們貪圖著現在的無所事事卻坐困愁城,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,在心底悄悄滑過焦慮。無計可施的最後,還是要出去面對四個歪倒的大背包。
僅僅只是搭個帳,此時此刻於我們而言卻是件大事。幾個人討論著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,能保兩頂內帳不溼而迅速搭好帳篷,能見度太低要掏頭燈。有人穿起溼淋淋的雨衣、有人宣讀菜單。
「妳要不要把裡面那件排汗衣脫了?這時候穿溼衣服出去太冷。」高義對我說。
我的排汗衣沒脫,外面罩著一件乾燥刷毛衣,貪心地想用體溫烘乾它。
「妳今天是生理期第幾天?」高義見我還是不斷地發抖,順口一問。
「第三天吧。」瓜瓜在一旁替我回答。
「我的雨衣丟在背包上沒有拿進來……有人可以先出去幫我拿嗎?」我衡量自己的情況,不敢沒有風雨衣就這麼走出去。
「妳待在帳篷裡好了,我一個人就可以搭帳。」瓜瓜轉過頭來跟我說。
「啊?不用啊……只要幫我拿雨衣進來就好了,兩個人一起搭比較快……」
「我跟高義可以幫她搭。」歷凡說。
「嘿,一個人在帳篷裡等很無聊吧?來,我有mp3,妳可以一邊聽音樂一邊等我們搭帳篷。」高義把mp3遞給我。
我看著瓜瓜一邊穿雨衣一邊尖叫、看歷凡打開帳篷拉鍊、看高義深呼吸一口氣,然後衝出去。
他們出去的時候,天已經黑了。
我在這個帳篷裡,只是坐著不動,聆聽三個人在風雨中喊話:「營釘!」、「快一點!」、「真他媽夠冷!」……更多時候他們沉默地動作著,窸窸窣窣的聲響,比雨打帳篷的滴答聲還要更清晰。
時間忽悠拉長了。
mp3還在手上,我甚至沒有解開纏在上頭的耳機線,只專心聽著他們動作的聲響,想像他們用發顫的手指把冰冷的營柱接起、搭外帳、插營釘、拉營繩。偶爾能聽見瓜瓜太冷而受不了的尖叫。有人倒抽了一口氣。
我什麼都沒有,但有一頂帳篷,三個隊友。
「我把妳的背包拖進我們帳篷裡喔,妳等一下,快好了……啊啊……」瓜瓜的聲音突然緊縮。
「怎麼了怎麼了?」什麼都看不見,我有些著急。
「沒事沒事,絆到繩子……」瓜瓜說。
我打開帳篷探頭,發現我們的帳篷就在一旁不到兩公尺處,瓜瓜撐著傘又跑過來,站在我的上方,說:「妳可以過去了。」
歷凡和高義等我出來,他倆一前一後便鑽進那頂帳篷裡了。
「我的衛生棉一天都沒換……」坐在搭好的帳篷裡,我說。
「是喔?」瓜瓜看著我,她的眼睛瞪得老大。
我坐在帳篷門邊,允許自己呆愣一分鐘,然後接過瓜瓜手上的雨傘,走出帳篷。胡亂向外走去,隨地脫了褲子,蹲在那裡,從胯下俐落地抽出衛生棉,遲疑了一下,冷風吹來的一瞬,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單手擰了它,感覺包覆的水和經血順沿手心手背流下,因夜晚可以假裝看不見而感到慶幸,隨手塞進褲子的口袋裡,草草換上新的衛生棉,褲子隨即拉起。閃進帳篷前,聽見對帳的高義和歷凡說:「明天要是繼續下雨,我們就不走了……」
活著的快感穿透身體
隔天清晨,我醒來。
在帳篷邊側,聽見鞋子踩草地的聲音,有人走來走去不知道在幹嘛。「天氣如何?」我問。「妳出來就知道了。」那人是高義。
命運之神實在很奇怪,前一夜明明意志消沉到不剩任何力氣,關鍵時刻卻翻盤。
拉開帳篷,陽光下青草的綠色很刺眼,我終於看清楚太平溪源的草坡,看清楚營地與溪流的走勢,天地裸裎,大剌剌迎接我的錯愕。歷凡忙不迭把溼淋淋的裝備都丟出來,它們被鋪在地上或掛在箭竹上,水珠滴下。記憶還很新鮮,前一天的痛楚驀地閃現。
這個早上,我們極盡能事地清算所有的溼冷。數不盡多少東西被攤開在陽光下,一件一件,從冰冷的大背包裡扔出,如條列的裝備表一項項細細檢視。雨衣雨褲翻面、普魯士繩解開、頭巾摘下、睡墊從帳內抽出、襯衫攤平在地上、襪子倒插在箭竹上……人人無不仰頭呼吸溫暖的空氣,藍天張牙舞爪的時候,乾燥的草地直想讓人翻滾。
「活著」的快感穿透身體,雨過天晴早已不是第一次,但每一次都被生存的真實耳提面命,約莫是前幾天的痛苦太清晰,有那麼一刻,我站在那裡,看著滿地的裝備發呆:痛苦和露水一樣,總會隨陽光蒸發。
「今天就等裝備曬乾再出發吧!」高義大刀闊斧地宣示,我們從容地整頓。
大半個早上,裝備等待暖陽遷徙,時間漫漫,風徐徐吹。
歷凡熟練地煎著蔥油餅,敲著鍋緣打下一顆蛋,鋼杯裡已經捲好了幾片,我咬下第一口蔥油餅時,瓜瓜煮的熱咖啡也好了。
三個人圍坐在這裡,遠處的高義伸了個大懶腰。「高義,過來吃早餐!」瓜瓜喊著。
如果不曾患難與共,這一刻不會如此彌足珍貴。
我瞇著眼直視太陽,這個我們連日朝思暮想的對象,再一次把晴天之可貴放在掌心上,輕易就原諒了昨日。

程靖芸攝影/果力文化提供
書籍資訊
◎本文圖片、文字摘自果力文化出版,劉崇鳳著作:《我願成為山的侍者》一書。山,就在那裡,就在心裡。每爬完一座山,就是一個新的自己走出山徑!
★愛山,曾是一則不能說的祕密⋯⋯
她曾經歷隱瞞家人偷偷爬山,充滿小小謊言的山林歲月;
她鍛鍊山野能力,找到與山從容相處的方式,
她是帶著孩子、女生爬山的「山女」領隊。
因為愛山,她走得很深,很遠。
山的給予如此無私,餽贈如此豐美,
她願成為山的侍者,傳遞山野的訊息。
作者愛山,大學登山社時就是一個纖瘦清麗但堅持全程負重登高的「扛霸子」,卻總須隱瞞爸媽、編織小小謊言交代行蹤——因為女生爬高山必須面對更多身心挑戰:家人反對、生理期不便、負重攀登的體力限制、因山野能力不如男性隊友而缺乏自信⋯⋯然而,這些都無法停止她對山的想望。
她知道,台灣這座年輕島嶼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,在地塊劇烈擠壓並刻鑿的皺摺之中,藏有無數大自然的奧祕:山容起伏奇險峻秀,短短半天自溪澗陡升至高海拔,每一步都伴隨精采的微觀世界;登上峰頂整座青島濃縮眼前,360度皆是不可思議的美景。
書籍資訊 請點此
◎本文圖片、文字摘自果力文化出版,劉崇鳳著作:《我願成為山的侍者》一書。山,就在那裡,就在心裡。每爬完一座山,就是一個新的自己走出山徑!
★愛山,曾是一則不能說的祕密⋯⋯
她曾經歷隱瞞家人偷偷爬山,充滿小小謊言的山林歲月;
她鍛鍊山野能力,找到與山從容相處的方式,
她是帶著孩子、女生爬山的「山女」領隊。
因為愛山,她走得很深,很遠。
山的給予如此無私,餽贈如此豐美,
她願成為山的侍者,傳遞山野的訊息。
作者愛山,大學登山社時就是一個纖瘦清麗但堅持全程負重登高的「扛霸子」,卻總須隱瞞爸媽、編織小小謊言交代行蹤——因為女生爬高山必須面對更多身心挑戰:家人反對、生理期不便、負重攀登的體力限制、因山野能力不如男性隊友而缺乏自信⋯⋯然而,這些都無法停止她對山的想望。
她知道,台灣這座年輕島嶼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,在地塊劇烈擠壓並刻鑿的皺摺之中,藏有無數大自然的奧祕:山容起伏奇險峻秀,短短半天自溪澗陡升至高海拔,每一步都伴隨精采的微觀世界;登上峰頂整座青島濃縮眼前,360度皆是不可思議的美景。
書籍資訊 請點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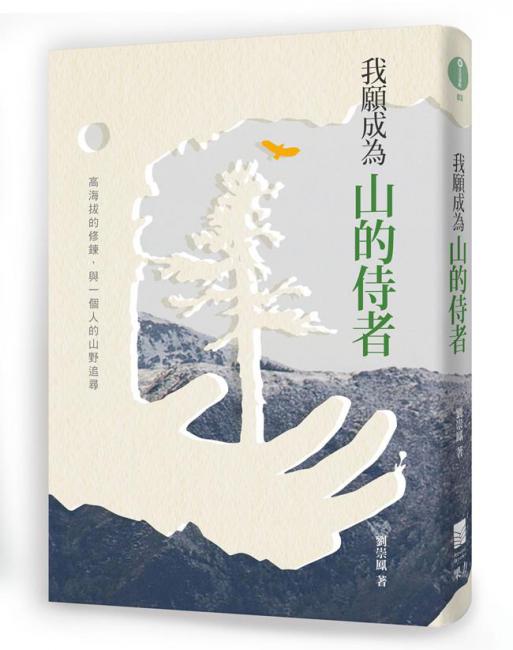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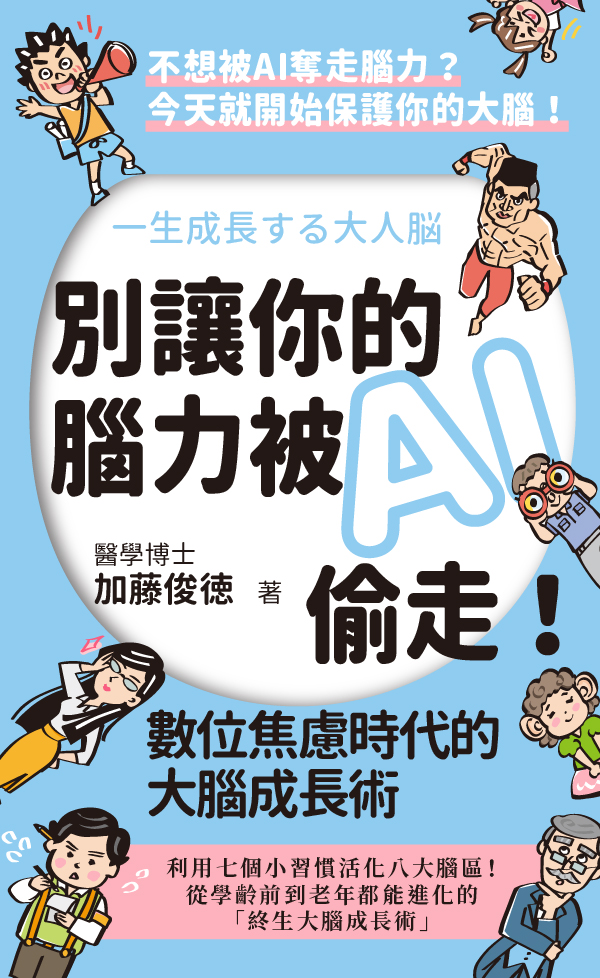

運動星球
96歲美國阿公越跑越快 打破自己去年跑山紀錄
2016-06-24
超過90高齡之後,照理說一個人應該行動越來越緩慢,不過這位美國阿公卻顛覆體能極限,居然打破自己的跑山紀錄!
據Runner’s World網站報導,現年96歲,來自賓州州學院市的喬治·艾茲維勒 (George Etzweiler),上週六完跑了在新罕布夏州舉辦的「華盛頓山路跑賽 (Mount Washington Road Race)」,這是他第11次參賽,也是連續第二年跑這場比賽。他的這次參賽,不僅打破該賽事年紀最大參賽者紀錄,更超越自己去年同場賽事紀錄有5分鐘之多!
這場華盛頓山路跑賽全程7.6英里(約12公里),路程長度看起來不怎麼樣,不過這可是一場全程都是上坡的路跑賽,總爬升4,727英尺 (約1441公尺)、平均縱坡有12%的山徑賽,就算今年的男總一Joseph Gray,他也要花上58分16秒的時間才能跑完。艾茲維勒爺爺則是以3小時23分15秒完跑,與他去年的成績3小時28分41秒相比快了5分多鐘,不過他賽後還是告訴跑者世界的記者說,他應該還可以跑得更好。
「顯然,我還是沒有很相信教練的指導或是我自己的能力,所以我沒有在一開始就用力跑,」艾茲維勒爺爺說。「老實說,我在這場比賽全程都沒有太費力,所以跑完之後也還覺得有餘力,這對我跑這場比賽來說應該是好事。」
艾茲維勒爺爺將今年的進步歸功於投入更多的跑步訓練:他就近在像華盛頓山這樣的山坡,每週進行三次的上下坡跑步訓練,並在他的日常鍛鍊中加入了阻力訓練。最近他在一位教練的指導下,完成了一項為期12週的阻力訓練,從而幫助他改善了一些身體穩定性的問題。
這樣的訓練似乎也幫助艾茲維勒爺爺在比賽後能夠迅速恢復,因為他在賽後隔天就立馬花了三天在比華盛頓山陡峭的山脈中健行,做為他來新罕布夏州度假的一部份行程。
「我很開心我還活著。我兩個孩子敦促我去爬山爬了三天,」艾茲維勒說。
「不過,當我在這些山裡健行時,我的腦海裡則一直在盤算著,看我明年能做些什麼來跑得更快一些,」他補充說。
艾茲維勒祖孫三代一起完成了週六的比賽。喬治70歲的兒子拉瑞,和40歲的孫子羅伯特,都成為近年來促使喬治參加一些比賽的推手,並一起陪他上場完賽。
1989年,在他兒子的督促之下,艾茲維勒爺爺在69歲時跑了他人生的第一場華盛頓山路跑賽。在參賽的11年之中,他贏得了七次年齡組別的冠軍,雖然在最近幾年,他這個年齡組通常只有他自己一個選手。
艾茲維勒曾經在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擔任電子工程學教授有37年之久。在他49歲之前,他從來沒有一口氣跑過一英里以上。當他開始跑步之後,他減掉了15到20磅。五年前,當他開始吃全素,他又減掉了額外的幾磅體重。
但他還是把他的成功歸功於好運。
「我能夠把事情做好,真的是因為運氣好,」艾茲維勒說。「我覺得我的一生充滿了福氣,常常有好事發生在我身上。」
艾茲維勒爺爺打算繼續參加華盛頓山路跑賽直到100歲,他開玩笑說,他那一場想要風光謝幕。
「2020年,我100歲,當我衝過終點線時,我大概就會馬上倒地不起了」他笑說:「我已經告訴賽事總監說,那年要記得幫我訂一台靈車做準備。」

在賽道中的George Etzweiler ©MEG SKIDMORE / Runner's World

運動星球
Volvo LifePaint 是夜騎福音
2016-05-10
晚上騎單車在馬路上,常有被無心的汽機車撞到的危險。Volvo 最近發表了LifePaint,是與英國廣告商Grey London和瑞典新創公司 #Albedo100 合作的產品,後者就是一家專門研發反光噴漆的公司。

這種噴漆是無色透明的,可以持續一週,單車騎士可以噴在單車上,也可以噴在包包、衣服、鞋子上面,當車燈一照到噴漆上,馬上會反射出強烈的白光,只要噴的面積夠大,這時不被注意到也難,當然,跑者或行人若要在夜間外出也可以使用。

明亮環境(左)和黑暗環境(右)的反光視覺效果。
其實要改善單車在夜間的被注意度,已經有許多公司做了不同的嘗試,例如在輪框上加上LED燈,或是將整個輪框都包覆反光材質,這些也讓騎士們有更多安全選擇,但看起來最厲害的,還是這種可以到處噴的LifePaint。

VOLVO LIFEPAINT噴上後屬於無色透明的狀態,並不會改變原本衣著外觀,只有光源直接照射時會反光。並且,請放心,它是可以使用肥皂輕鬆清洗的。

Volvo公司一直專注在強調保護乘客的安全,這種精神也延續到路上的行人和單車騎士,藉由LifePaint的發表,Volvo同時宣誓了要在2020年達成沒有人會在路上被Volvo車撞死或重傷的願景,LifePaint是其中一項對策。
剛開始,Volvo LifePaint只有在英國六家單車店販售,若成效不錯,之後會推廣到世界各國。
Volvo LifePaint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