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運動星球
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 黃丞逸拚聽奧、玩鐵人,更要幹大事
2021-05-10
去年 12 月初黃丞逸完成屏東大鵬灣鐵人三項後,馬不停蹄地又在臺北馬拉松半馬組破了個人 PB,在耐力運動表現上皆有好成績的黃丞逸,其實卻是一位爆發力十足的「羽球聽障國手」!對黃丞逸來說,2020 年無疑是他人生的轉捩點。

目前黃丞逸一邊在體育署擔任公務員,一邊在臺大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系攻讀碩士學位,而同時他也是位羽球聽障國手!已擁有多重身分的他,在今年完成屏東大鵬灣鐵人賽事後又多了一個「被羽球耽誤的鐵人」的頭銜。

羽球國手之路
「2009 年我爸帶我去看台北聽障奧運。」黃丞逸說,當時他爸爸只問他一句:「你要不要試試看?」這句話意外地開啟了黃丞逸的羽球之路。

半路出家的丞逸就這樣一頭栽進羽球訓練,儘管辛苦他也都能正面積極地將肌肉痠痛看待成一件幸福的事。當時黃丞逸不是在練習,就是在前往比賽的路上,他身邊的友人開玩笑形容他是位不折不扣的「運動狂人」

現在的黃丞逸儘管工作忙碌,但總能在工作和學業中找出空檔去和羽球校隊一塊練球,期望力拚今年三月的聽障奧運資格賽!「(聽障奧運)有上就去!沒上就去跑鐵人!」黃丞逸替自己訂下目標,完全表達出專心訓練的決心。

運動狂人兼學霸
黃丞逸大學雙主修臺大政治系與社工學系,目前則就讀於臺大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系碩士班。他認為,每個人都有成為「陪伴他人」或是「被陪伴」的角色,而社工便是這樣的角色,「每個人都有需要被幫助的時候,人是群居動物,也都有脆弱的時候,看待每個人的眼光,不應該是不一樣的,也不應用主觀意識去評斷他人,即使他人的樣貌不符合社會大眾一般期望。」黃丞逸說:「每個人顯現的樣子,背後都有養成經驗和背景故事,需要的是更多同理心而不是汙名化。」
他亦強調,社工這個角色除了是他人的支柱或力量,但其實他們也更需要適時的釋放情緒和接收旁人的關心。「看不到,不等於不需要。」

黃丞逸在 8 個月大時,生了一場重病,1 歲被診斷出失去聽覺,並在 5 歲時開刀裝電子耳,「對我來說,聽障就像近視一樣。」丞逸樂觀表示,以當時才發展 7 年的技術來說,在臺灣要開刀裝電子耳的案例少、技術新、費用高,無疑是個冒險的決定,所幸手術成功,術後追蹤檢查結果都不錯。
黃丞逸研讀社工領域,加上同為身障人士,不僅透過大學歷程讓他對未來設下許多目標,也能用抗壓和樂觀的心態適應社會衝擊。大學畢業後工作幾年後,丞逸決定重返校園完成碩士學業,其中也將論文題目以推動無障礙設施為主,盼將所學化為行動,實質地回饋社會
「愛運動‧動無礙」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 盼貢獻所學改變社會
在某一次的因緣際會下,黃丞逸認識了姜義村教授的「愛運動‧動無礙」團隊,這個「偶然」也讓丞逸對未來,產生了新的目標。「我希望能建立完整無障礙運動設施,提供身心障礙者運動的環境不只有透過『工作坊』形式短暫提供,而是長久存在。」他說:「因為『人會忘記』,所以推動無障礙設施的計畫必須持續進行,讓這項計畫細水長流,而不是只成為一波熱潮。」丞逸認為,目前雖然已開始有團隊執行類似無障礙設施項目,但總體來說,臺灣尚未彙整出完善的依據和考量。「希望自己可以藉由碩士所學專業,朝這個目標推動執行。」
「能影響多少人我不知道,一個觀念的養成要多少時間我們也不知道。與其想著什麼時候能做到,不如做了再說。」丞逸語氣堅定:「希望有天能看到社會大眾面對身心障礙的人,是像呼吸一樣自然的相處和感覺,而不是投以異樣眼光和預設立場。」

「我們都是一群很平凡的人,但是我們都能做出不平凡的事。」
黃丞逸說,他常用這句話作為自我價值的期許,盼自己未來能放慢腳步,好好學習,「人生不只是運動、羽球,還有很多價值需要被實踐。」丞逸希望自己能為倒數幾個月的聽障奧運備戰的同時,也能在無障礙設施的推重中盡自己的一臂之力。

文章出處/don 1 don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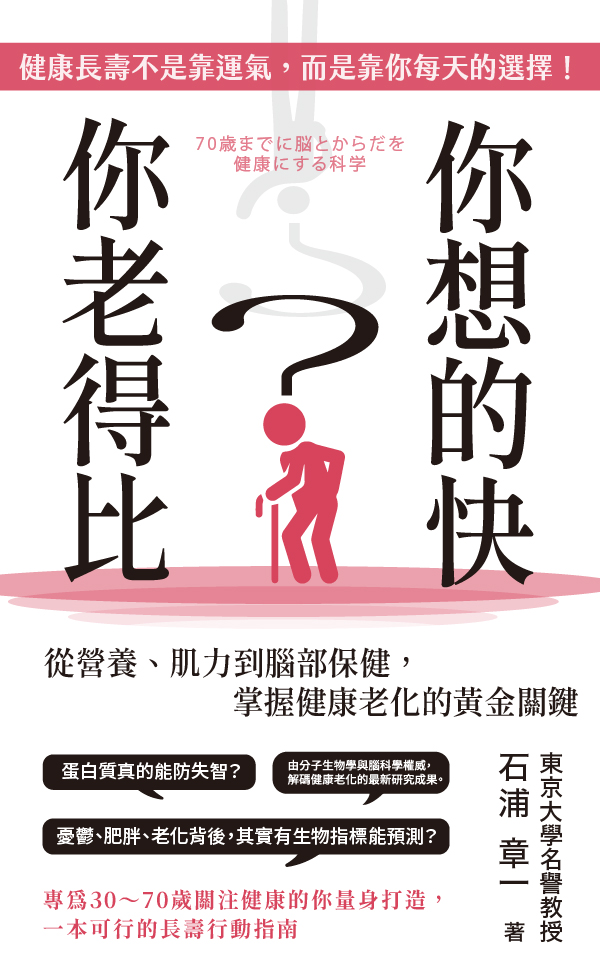

運動星球
CHUMS日本福袋空降來台 12/22-1/1現身GO WILD野聚戶外
2018-12-20
耶誕節、新年緊接著到來!在日本,新曆新年是全年度最重要的大節日,相當於華人的農曆新年,日本人多會到廟裡祈福,許多百貨也會在此時推出各式福袋。深具日系風格的FUN OUTDOOR潮牌CHUMS,趕在日本新年前規劃一系列商品福袋,將日本的新年氣息原汁原味空降來台,12月22日至明年1月1日可於GO WILD野聚戶外與指定店點購買。

CHUMS日本福袋空降來台 12/22-1/1現身GO WILD野聚戶外
正月初一的新年春假期間,日本人多會到廟裡祈禱新的一年平安和福氣,許多百貨公司趁此時提供高質感且極優惠的各類福袋讓消費者購買,象徵給新年的好兆頭;而台灣許多日系品牌也會跟上這波風潮販售福袋,給台灣民眾感受日本過新年的風氣。
CHUMS最為人知的是源自露營生活的設計商品,像是火紅的Booby烤盤組、露營馬克杯等;另以俏皮有趣為出發點的服裝設計商品、包袋類商品也十分受歡迎。而CHUMS將於12月22日起至明年1月1日,特別針對配件類以及服飾類做福袋販售,並將於GO WILD野聚戶外與指定店點獨家販售,讓消費者享受最純正的日本習俗。

CHUMS推出福袋商品,將於12/22-1/1限量發行
在日本生活超過10年的福袋專家Chris,不藏私分享福袋的搶購指南:福袋有許多販售種類,想得到的商品在日本都有做成福袋(例如家電、藥妝、食品等)。在日本,新年福袋的重要性就像是1111的優惠搶購一樣,不同的是無法預測裡面的商品,相對更有驚喜的感覺。
這次CHUMS福袋將配件與服飾分開販售,是要讓喜愛不同商品的民眾有更多選擇,例如配件類福袋更有可能獲得CHUMS的經典露營馬克杯、太陽眼鏡帶、甚至日本限量Booby不鏽鋼杯;服裝類更有可能獲得市價近六千元的防水外套、音樂祭必備的披風雨衣等。Chris表示,這次的CHUMS福袋用心程度,更可以被稱作「有史以來在戶外界中最推薦的福袋」。
價格上則以分波段販售,可自行選擇高價位或低價位。配件類福袋售價分別為1,000元(商品總值3,500元)與3,000元(商品總值10,000元);服裝售價2,500元(商品總值8,500元)及5,000元(商品總值16,000元)。

CHUMS福袋將配件(右下)與服飾分開販售,是要讓喜愛不同商品的民眾有更多選擇
關於CHUMS
一位科羅拉多河的導遊,在科羅拉多河觀光帶團的時候,因為太認真了,總不經意的丟失昂貴的太陽眼鏡,因緣際會決定研發舒適好搭的太陽眼鏡固定帶。沒想到竟然熱銷,研發者 Mike Taggett 在1983年決定成立戶外休閒裝備品牌CHUMS來讓更多人認識這項產品。Mike思考應該要設定一個CHUMS吉祥物來傳達品牌理念,左思右想決定將Booby bird做為品牌宣傳的吉祥物。Booby是極少見的紅腳鰹鳥,廣泛分布於太平洋、印度洋及澳洲等溫帶及熱帶地區附近的海島上。Mike認為以Booby bird做為品牌標誌,能傳達出CHUMS象徵的伙伴、友善、信任和快樂等理念,並展現出品牌對大自然保育的熱誠與尊重。與CHUMS一起Fun outdoor,找到戶外的自在與生活形態,你的生活你做主。
資料來源/GO WILD野聚戶外
責任編輯/Dama

運動星球
New Balance推出極輕保暖科技 讓你在城市戶外都穿梭自如
2018-11-15
週間穿梭城市、週末嚮往親近自然,是許多都會男女愛好輕旅行的「雙棲」生活模式,New Balance本季推出HeATloft極輕保暖系列服飾及Fresh Foam Cruz Decon避震跑鞋,提供絕佳保暖度及運動性能需求,無論走出戶外或城市漫遊,皆能恣意無阻,穿梭自如,打造「無所不Chill」的機能輕旅「型」。

New Balance HeATLoft輕量保暖服飾,創造滿足運動及休閒穿搭等多元需求的冬季輕旅單品。
融合休閒與運動機能,New Balance打造全新HeATloft保暖科技,採用機能性紗線編織一體成形,特殊雙層織法緊鎖身體熱能,比傳統絨毛布更保暖、更輕量,並添加彈性纖維強化運動時的延展度需求,全系列於外型上以簡約剪裁搭配具都會感的菱格紋元素,包含保暖針織連帽外套、長袖上衣及長褲,創造滿足運動及休閒穿搭等多元需求的冬季輕旅單品。

New Balance本季推出HeATloft極輕保暖系列服飾,為全新面世的極輕保暖科技。
Fresh Foam Cruz Decon全新面世
承襲Fresh Foam Cruz系列簡潔鮮明的次世代潮流跑鞋氣息,New Balance本季為Cruz Decon緩震跑鞋加入解構元素,透過流線設計注入簡約風格,將簡約紋理取代鞋身N字 logo 原有位置,搭配運用針織與麂皮的異材質拼接,巧妙為整體設計創造嶄新連貫性,並突顯鞋型的流線美感;鞋底加載New Balance標誌性的Fresh Foam緩震中底,配合舒適後跟環狀軟墊支撐與便捷穿脫的襪套式設計,輔以鞋面絕佳包覆力,彌合運動與都會時尚界線,為日常穿搭至運動時刻的恣意轉換,打造多元搭配的跑鞋選擇。

New Balance Fresh Foam Cruz Decon避震跑鞋透過流線設計注入簡約風格,將簡約紋理取代鞋身N字 logo 原有位置。



